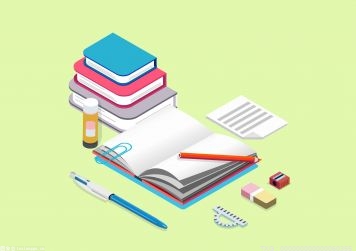sansa2025
sansa2025
9
2025-08-06
近日,阿里系外卖APP“饿了么”因随机给用户免单而数次冲上了热搜。在活动期间被选中的免单用户,订单金额将被直接退回到平台钱包,虽然不能提现,但下次下单可以直接使用。对用户来说,这非常刺激神经。 抓眼球的另一面,舆论和口碑常常是一把双刃剑。能够通过热议产生品牌和流量红利,也能因为套路太多,体验不畅而让用户失去耐心。 饿了么本次活动从神秘到热闹持续了两天,第三天就开始基于用户体验呈现出动作变形:一分钟的免单时间里,开始陆续有网友在社交网络写消息表达不满,他们吐槽在规定的一分钟时间里无法提交订单,临门失去参与“抽奖”的机会。有些重新下载饿了么的老用户再次删掉了APP,表示自己只是那个被喊来“砍一刀”的人。 总的来说,这是个传播尚可,但又显得有些仓促的运营。撒钱赚吆喝的背后,还是要自己的ROI算得过来账。而投入背后实际的留存和复购,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检验。 高举高打的营销策略背后,是饿了么早已失守外卖半壁江山的深层焦虑。 01 饿了么早已掉队多年 早在2018年,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把饿了么卖给阿里时期,饿了么的增速就已经开始呈现出不敌美团的趋势。并入阿里后,饿了么在2018-2022年4年的时间里,DAU长期徘徊在张旭豪时期的1000万左右(疫情后数据1500万左右)。 大比分落后 说起来,各个时期阿里空降饿了么的职业经理人们,这么多年只保证了饿了么的数据没有暴跌,但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增长。与此同时,美团4年时间数据翻了数倍,达到了饿了么难以超越的8500万DAU。 如今,再把1500万DAU的饿了么和8500万DAU的美团放在一起讲,对饿了么来说,是一种表扬。双方长期呈现出的大比分悬殊,早已宣告了这场商战的结果。 当行业增量空间有限,内卷式竞争把赛道玩家拖入零和游戏。零和的残酷在于,双方或多方都吃不饱,只有割别人的肉,才能为自己换来新增长。就在饿了么推出免单活动前夕,某职场社交APP爆出,美团定向针对双端用户(手机里同时有美团和饿了么2个软件)发优惠券抢用户。商战打到了家门口,饿了么要解眼前的兵临城下。 远水近渴 虽说远水解不了近渴,但假如不提前布局“远水”,就会永远活在“近渴”之中。 饿了么的免单活动,发的是真金白银。能够很实时地从流量角度,拉新用户使用他们的APP,同时,还能够让已经流失了的老用户重新回来。免单退款到平台钱包,意味着针对免单用户,还多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复购,围绕这个用户群会100%提升复购率。短期看,这很聪明,但成本也高。 反观美团给用户发券,给商家发补贴的策略,短期看不那么立竿见影。但长期会增加供给侧的竞争力。普通外卖用户虽然不清楚在线产品的运营逻辑,但是基于地理位置,家附近餐厅一搜,哪个APP选择多,他们还是很容易发现的。 O2O是很复杂的业务,光有钱不行。大公司走马灯一样更换的职业经理人,魄力上比不了王兴这样的狼性创业者。前者遇事先写邮件,后者能够直接决策。虽然阿里现任本地生活CEO俞永福在内部信中说这条赛道不拥挤,但他没说的是,竞争对手太强了。从供给侧到需求侧,饿了么已经掉队很多年了。 02 四年换了三个老板 阿里系并购业务的融入路径,常常呈现出人们脑海中“阿里式收购”的高举高打:给钱,但有极强的控制欲。 收购,接管,派出业务线高层,派出财务和人力资源团队。在实际的运营磨合中,在每个原有团队的中层架构基础上,再空降一个淘系的业务leader。 饿了么融入阿里,走的也是这个路径。 干将试错三年 2018年阿里正式收购饿了么2个月后,由当时阿里15年的老员工昆阳(王磊)接手。昆阳属于阿里自己从零到一培养出来的管理干部,先后在B2B广告部和无线事业部工作过。2013年任淘点点事业部总经理,2015年任阿里健康CEO。他曾在2020年任本地生活CEO期间,和时任淘宝天猫总裁的蒋凡一起,晋升成为M7/ P12的高级管理者。 昆阳在本地生活总裁的位置上履职三年期间,文化上信仰阿里三把斧(揪头发、照镜子、闻味道)的昆阳曾经信心满满地认为,张旭豪时期的饿了么和美团竞争,是美团吊打饿了么,2楼打1楼。接入阿里后的饿了么美团竞争,必然优势反转,转为饿了么从6楼打2楼(美团)。[1] 昆阳没能让饿了么翻盘。他在任的3年,正是外卖业务被美团强势碾轧的三年,饿了么DAU数据不但没有明显增长,反而有几次跌破了买来那会的1000万。有人不理解昆阳业务数据做得那么差,为什么在本地生活那么稳?一位阿里前HR给出了他的分析:因为内部培养,根正苗红,有“阿里味儿”。 这位HR甚至还举了一个例子用来对比,讲了当时主张业...